你无法确知自己在为了什么奋斗
原文:You don't get to know what you're fighting for
2015 年 5 月 17 日
我最近的几篇文章可能给你们造成一种印象:我似乎很清楚自己在为何而奋斗。如果有人问你:「嘿,那个叫 Nate 的家伙那么拼命是要干什么?」你可能会回答诸如「增加人类生存的几率」、「终结可避免的死亡」或「减少痛苦」之类的话。
但并非如此。我是说,我确实在做这些事,但这些都属于否定式的动机:我对抗阿尔茨海默病,我阻止人类灭绝,但我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然而事实是,我也不太确定。我确实在追求某种东西,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我对我所为之奋斗的事物抱有许多感情,但我发现它们相当难以言表。
实际上,我非常怀疑是否有任何人真正清楚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尽管似乎有许多人自认为清楚,而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之一。
当我写那篇关于理性的文章时,一位评论者回复道:
我只想先指出一点,
是否能合理地推理与原本的推理目标关系不大。
以及
这种理性不是要改变你的目标方向,而是旨在提升你能前进的距离。
这两种说法,如你所知,都是善意的谎言。在思考如何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目标本身发生改变甚至消失,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如何最好地侍奉上帝」可能最终导致放弃信仰。
「如何让我与伴侣的关系幸福美满」可能引向发现对方是个我应该赶紧远离的自恋混蛋,或者发现我们俩都该另寻佳偶。
「如何帮助我的社区脱贫」可能转变为「如何尽可能地赚钱」,以便能尽可能多地捐款。
这个观点很精辟。人类有一种众所周知的能力:开始时追求某个目标,但随着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会发现眼前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这正是许多故事的核心情节(例如《基地三部曲》、《德累斯顿档案》和《永不结束的故事》)。你以为自己正在追求的目标,很可能经不起仔细推敲。
我声称,即便你认为你的目标简单、客观、显而易见、高尚或精妙,这一点依然成立。正如一位立志行善至上的有神论者,在认定即便没有神祇的授命、人类亦应繁荣昌盛之后,可能会转变信仰一样;一位致力于实现最大善的功利主义者,也可能最终发现其哲学理念本身便充满矛盾,无法自洽。
事实上,我怀疑这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人类当前的哲学发展阶段是这样。
宣称「我是一个彻底的享乐功利主义者」,并觉得自己完全清楚自己看重的是什么,这听起来美好、清晰又简单。但是,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算作是心智?什么算是偏好?偏好是根据谁的解释、通过谁的程序提取出来的?你是否觉得有义务去创造那些尚未存在的人?如果同时运行一个心智的两个副本,这个心智会变得更重要吗?我怀疑这些问题不会有客观的答案,而主观的解答会很复杂,并且将取决于我们看重什么——既然如此,「彻底的享乐效用」就并非真正的答案。你可以声称自己在为效用最大化而奋斗,但目前来看,这仍只不过是贴在一个我们还不太懂得如何表达的复杂事物上的简单标签罢了。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表达它,我也怀疑大多数人实际上并不是彻底的享乐功利主义者。想象一下,你的一个老朋友吃了个三明治,这个三明治(意外地)改变了他的偏好,结果他整天就只想盯着一面白墙看,并且不希望被任何人打扰。你觉得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帮他找面白墙,并阻止别人打扰他吗?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下就能让他恢复到吃三明治之前的状态,你会按吗?我绝对会按——因为我忠于的不仅是眼前的这个心智,更是那个人、那段历史、那位朋友。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偏离了客观的功利主义框架,进入了一个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究竟在为什么而奋斗的领域。
如果我更忠于我的老朋友,而不是那个坐在白墙前的人,那么我是否也有义务去「拯救」那些天生就想「接入快乐机器」(wirehead)的人?我是否有义务影响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价值观?我是否有义务在婴儿长大成人之前,就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
我不是说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确信许多人都给出了答案。实际上,我确信有些人选择了一些足够简单的、武断的定义,然后硬着头皮接受了所有相关的推论。(「是的,我确实有点在乎石头的偏好!」、「是的,我就是要最大化婴儿的效用!」,诸如此类。)我这里虽然是拿功利主义者来说事,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道义论者、有神论者,以及其他所有自认为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奋斗的人。
我想说的是,即使你声称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而奋斗,即使你声称自己接受各种后果、愿意承受一切代价,你对此的看法也可能是错的。
没有刻在宇宙中一块石碑上的客观的道德。关于什么事物是「真正重要」的,也并不存在客观事实。但那是因为「重要与否」并非宇宙的物理属性。它是人的属性。
关于我们在乎什么,确实存在事实,但这些并非关于宇宙星辰的事实,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事实。
世上没有客观的道德,但同时,你的道德观也并非仅仅是你口头宣称的那样。一个人可能声称杀人无伤大雅,但他可能是在撒谎。心智只是大脑的一部分,因此,(a)不存在客观道德,(b)人们可能会误解自己真正在乎的事物,这两种情况可以并存。
关于你在乎什么,确实存在客观事实,但你并非天生就能了解全部。至少现在还不能。人类尚未具备那种内省能力,也尚未达到那种哲学成熟度。但人类确实有强烈且被充分证实的动机去说服自己,以相信自己在乎的只是些简单的事物——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人声称自己了解自己的真实偏好时,总显得有点可疑。
由此看来,我认为几乎没有人能够准确把握自己真正在乎什么。为什么?这源于人类价值观的起源。还记得「时间」试图创造一个追求健康饮食的心智,结果却意外地造出了一个酷爱盐分和脂肪的心智吗?我当然是在开玩笑,将自然拟人化是有风险的,但道理不变:我们的价值观源自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与历史中的无数偶然事件紧密相关。
现在,我很高兴「时间」未能成功塑造出一个纯粹的健身狂人。我的价值观是由一些笨拙的进程塑造的——将漫长时间与一片热带草原强加于一代代猴子,我并不完全认同其所有结果,但这些结果也正是我的评判标准的来源。我对美的欣赏、我的好奇心、以及我爱的能力,全都源于这个过程。
我不是说我的价值观是愚蠢的;我是说,你不应期望它们会是简单的。
我们是由巧合、境遇、死亡和时间锻造而成的千百种欲望的碎片。如果我们的价值观能用某种简短、简单的描述来概括,那反而会让人意外。正因如此,每当有人声称自己明确知道在为什么而奋斗时,我总会心存疑虑。他们要么是说服自己相信了某种谬论,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别误会,我们的价值观并非无法探究(inscruitable)。它们并非在本质上无法认知。如果我们能存续足够长的时间,最终很可能会把它们梳理清楚。
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的全貌。
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会迷失在黑暗中。关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掌握着大量的证据。大多数时候,我更喜欢快乐而非痛苦,更偏爱喜悦而非悲伤。我只是无法确切地描述自己正在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而且,要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确切的描述。至少现在还不需要。我无法确切告诉你我的终点在何方,但我绝对能看清前进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谈论那些否定式的动机——比如终结疾病、降低生存风险之类——要更容易些,因为在我不确定什么对自己而言真正重要的情况下,这些是我相当确信的目标。我不知道自己确切想要什么,但我很确定,我希望有人类(或后人类)能够存续下去,见证这一切。
但请不要混淆我正在做的事和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后者要难以描述得多,而且我并未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已经理解了它。
你无法确切知道自己为何而奋斗,但这个世界已经够糟了,糟到你并不需要完全弄清楚这点才能行动。
为了克服那种倦怠型内疚,我强烈建议你记住自己有为之奋斗的东西,但同时我也得告诫你,不要相信自己已经确知那究竟是什么。你大概率并不知道,而且随着你对世界了解得越多,我想你的目标也会随之演变。
最后,我引用 Matt Rhodes 的一幅漫画作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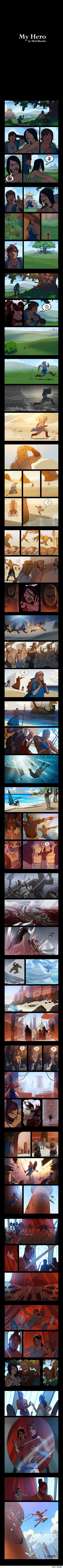
(来源)